2015年4月13日,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德國逝世,享年87歲。

這一天和以往任何一天沒有任何不同,人們行走、吃飯、穿衣。寫作的還在寫作,閱讀的還在閱讀,耕田的還在耕田,蓋房的還在蓋房。沒有人會想到,那個已經被我們遺忘的大師格拉斯正在一個遙遠的城市慢慢死去。
看到這條消息,我先是震驚,震驚他還活著。
我在書櫃裡找到了他的《剝洋蔥》,它穩穩地躺在那裡。書封還沒有拆。
就這樣,我無比愧疚地打開了《剝洋蔥》。這是我第一次真正走近格拉斯。
《剝洋蔥》是格拉斯沉黙了六十年之後寫的回憶錄。此時的格拉斯已經是個七十多歲的老人。
這些回憶就像沉積在海底的碎石泥沙,一直潛伏在他的內心。對格拉斯來說,是歷史,也是現實。
通過這本書,你可以比較全面地瞭解格拉斯,瞭解他的沉默,和沉默的悲傷和無力。
他冷靜地站在第三人視角審視著自己,他一會兒走過去,一會兒又抽身回到現在。他是第三人,他在看著兩個叫格拉斯這個名字的人。
他和所有這個時期的孩子一樣,懵懂、叛逆,嚮往自由,崇拜英雄。
「在餐桌上,我們希望得到船形帽,絲巾腰帶和肩帶在內的全套制服。以為這樣就可以擺脫家裡壓抑、沉悶的小市民氣氛,擺脫父親、擺脫了櫃檯邊顧客們的閒話,擺脫了狹窄的兩居室住房。」
二次大戰開始,他完全自願地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

但他從未原諒過自己對正義的漠視,和對納粹的盲從。雖然在戰爭中他沒開過一槍,雖然當時他只有十七歲。
「……自稱當初無知並不能掩蓋我的認識:我曾被納入一個體制,而這個體制策劃、組織、實施了對於千百萬人的屠殺。」
這樣的懺悔,在他心底藏了六十年。
他說,「心裡真想處決他(指少年的自己)。」
我想到了西蒙·威森塔爾《寬恕》裡的卡爾,那個躺在臨終醫院裡的青年党衛軍,他只有二十一歲。
他和格拉斯一樣,先是懵懵懂懂地參加了青年團,然後又懵懵懂懂地參加了党衛軍。
不同的是,他參與並被要求屠殺了一批猶太人。臨終時,他想求得寬恕,於是,命運安排身處集中營的西蒙遇上了他。
在這本書中,格拉斯還深情地回憶了那些活在他記憶裡的人,用語詞調動想像教他們烹飪的老師;寧願給大家洗大便池,也不肯拿起槍,高喊「這事咱不幹」的同伴;還有木訥,每天系著圍裙為一家人烹飪食物的父親,以及他著墨最多最愛的母親。
是她的藏書和她的愛庇護了小小格拉斯,是她打開了他的世界。
就在那狹小的,他曾一直想逃離的兩居室裡,有一個地方卻成了格拉斯的避風港,在客廳的一個角落有媽媽一隻書櫃。
他的母親愛夢想,愛讀書,她的手會彈鋼琴,也會沾了口水數鈔票。她始終相信自己的兒子是個有天賦的藝術家。
最後,她是患了癌症死去的。格拉斯用處於兩端的事件對比著敘述,來抒寫他對母親濃到化不開的愛。
他把新詩交給出版商,美好前程正緩步到來的時候,媽媽卻在遠方的城市慢慢老去;妻子安娜赤腳在木地板上翩翩起舞展示青春的時候,遠方的城市,媽媽正慢慢死去。
疼痛與命運的無常躍然紙上。
從書中看,影響格拉斯一生的主要有兩件事,一件是他對自己,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為納粹的幫兇而存在的不安和悔恨,另外一件就是他的閱讀。
這也是我很感興趣的部分。
他提到的書目我都列了出來。對他有影響的書,我都仔細作了標注。這些書有的我讀過,有的沒有。
看到我讀過的書,那個小格拉斯也讀過。我是如此激動。就好像誤入陌生人群,正慌張無措時,忽然瞥見角落有個人在溫暖地注視著我,興奮、狂喜。
王爾德的《道林·格雷畫像》、福克納的《八月之光》、喬伊絲的《尤利西斯》、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
格拉斯的文字不是寫出來的,是一筆一畫刻出來的,他把他的雕刻技藝也用在了寫作上。
那個在戰俘營裡,因沒有食材,就用語詞調動想像,教他們烹飪的老師,他不但教會了格拉斯烹飪,還教會了他通過想像請客,請過去的,和未來的人坐在一張虛構的桌子邊,品嘗一桌好菜。
還有,那個月夜,他的初次,草垛,姑娘臉上的雀斑;還有,那個每天在回屋前,先在遊廊上和他親熱的跛腳女孩,等等,這些細節,都在輕輕撩撥著我的記憶。
Cover: 《剝洋蔥》(Peeling The On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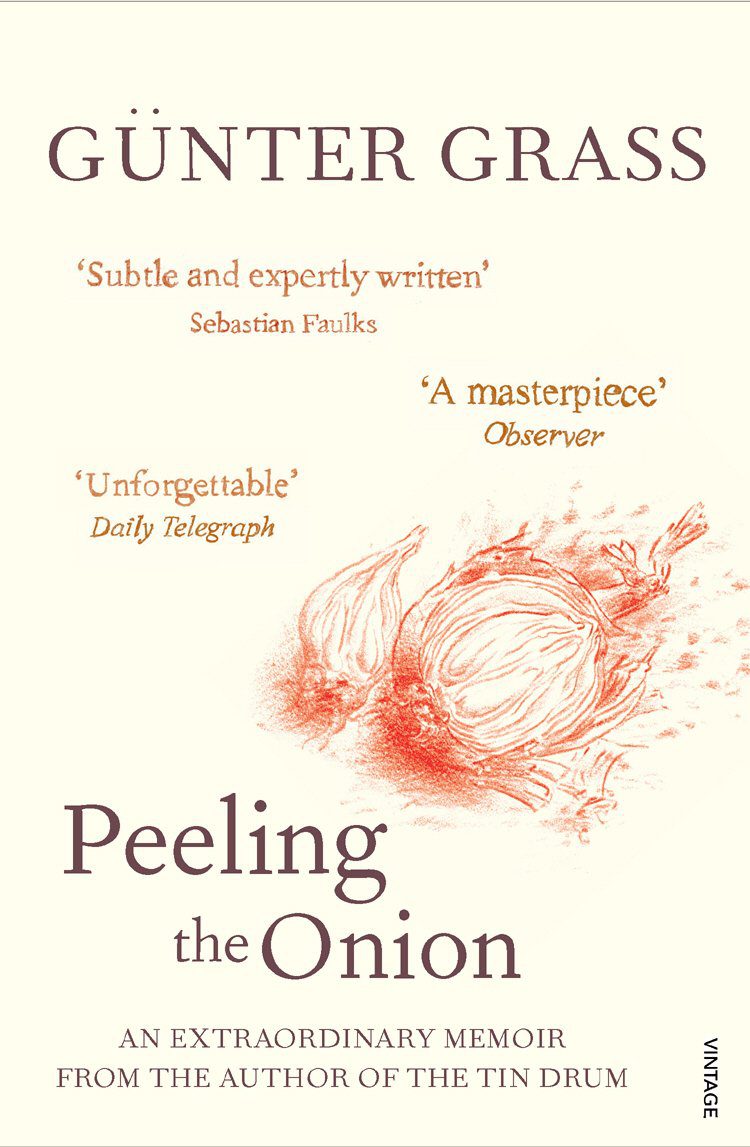
No comments yet. Be the first one to leave a th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