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區行政長官帶著一幫全副武裝的士兵和差吏來到奧貢喀沃家院子時,奧貢喀沃已經吊死在院子後面的一片矮樹叢裡。
《這個世界土崩瓦解了》,這是我第一次知道阿契貝Chinua Achebe。
我在網上一遍一遍搜阿契貝的名字,驚訝地發現他竟然沒有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
朋友說,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分兩類,一類靠諾獎證明自己,一類由他們來證明諾獎。阿契貝沒有獲得諾獎,那是諾獎的遺憾。
那天下午,我坐在家裡陽臺上的圈椅裡,打開了書。溫暖的陽光穿過窗玻璃打在書頁上,樓上窗外琳琅滿目的衣服在書頁上投下濃淡不一的影子。

就這樣,我走進了非洲。走進了烏姆奧菲亞這個遙遠的村子,我目睹了奧貢喀沃的一生。
奧貢喀沃的父親一生沒得到什麼頭銜,死了還欠了一身的債。
奧貢喀沃卻靠勤勞和勇敢在周圍九個村贏得了榮譽和地位,擁有兩個裝滿木薯的糧倉,娶了三房妻子,並得到了兩個頭銜。
鄰村為了避免戰爭,將男孩伊克美弗納給了他們村,族裡決定,伊克美弗納交由奧貢喀沃暫為看管。
雖然奧貢喀沃從不表露感情,但卻能看到他對孩子的疼愛。
奧貢喀沃出門總帶著這個孩子,教他種田,教他打獵。他們以父子相稱。
伊克美弗納在他們家住了三年。族裡決定要處決伊克美弗納了。
一群人跟在伊克美弗納後面,其中就有奧貢喀沃。快到鄰村交界的地方,走在伊克美弗納後面的人突然用刀從背後砍向伊克美弗納,他驚愕地轉身,向奧貢喀沃跑去,邊跑邊喊,爸爸,他們要殺我。沒想到,奧貢喀沃的刀也揮向了他。

在這本書中,類似這樣直擊人心的片段還有很多,閉上眼睛,就會像電影一樣一幕一幕重現。
奧貢喀沃的第二任妻子是個多災多難的女人。
年輕時,她愛上了奧貢喀沃,但那時奧貢喀沃很窮,她嫁給了另外一個人。
兩年後的一天早晨,她頂著月色到河邊取水,奧貢喀沃的家就在這條河邊,她敲開了奧貢喀沃的門,奧貢喀沃默默地把她領上了自己的床。
後來,她生了好幾個孩子,都在嬰兒期夭折。族人認為這是惡靈迴圈投胎,對她那個後來好不容易活下來的女兒百般防範。
有一天,女兒突然發燒,晚上,女祭司走進他們家院子,要帶走孩子。
在哀求無用的情況下,可憐的女人,她悄悄地跟在背著女兒的女祭司身後,從深夜跟到清晨,眼看女祭司背著女兒走進了洞穴,她心痛,但卻束手無策。
她守在洞口,暗下決心,只要女兒在洞穴裡喊叫,她就沖進去,死,也得陪著孩子一起死。這時,奧貢喀沃卻提著刀出現在她身後。
阿契貝說,她知道,女兒安全了。
阿契貝的講述是不動聲色的。他的語言簡潔,夯實有力。用朋友的話說,他寫下的每個字都很結實,就像奮力砸向桌面的拳頭。
讀這本書,常常會有空間、時間穿越的恍惚,就好像我在聆聽,而不是閱讀。

我看到阿契貝的眼神越過爐火,越過牆,越過馬路、草地、河流、森林……在爐火輝映下,他的臉忽兒紫忽兒紅,眼睛裡的光,忽明忽暗。
他把我帶入其中,震撼、哭泣,卻都由不得我。
可憐的奧貢喀沃,因誤殺人,攜妻契子逃往母親娘家七年,回到家鄉,家鄉已經面目全非。
白人建起了教堂、商場、學校,劃分了行政管理區,建起了法庭。
伊博人走進了學校,走進了教堂。
因為燒教堂,奧貢喀沃被法庭逮捕。最後,他沉默地向一個教徒舉起了刀。
阿契貝在結尾這樣描述,教區行政長官處理完奧貢喀沃的遺體,決定寫一本書,這本書的書名將是「尼日爾河下游地區原始氏族的平定」。
終於,白人成了伊博人的保護者,而倖存的伊博人都佩戴上了被保護者的胸章。
奧貢喀沃的死,意味著伊博人自主獨立的世界已經土崩瓦解,隨之而起的是一個以保護者的姿態行走在這片土地上的白人的世界。
這是一個人的命運,也是整個民族的命運。世上從來沒有永遠穩固的城堡,隨著歲月的變遷,如果不加以修繕,它只會變得越來越脆弱。風總會吹進來,單靠抵擋毫無用處。
阿契貝說,「伊博人在戰場上拼殺,輸了。他們奮力抵抗,還是輸了。」
這無關民族傳統的好壞,無關民族素質的本原是否低劣。阿契貝在《非洲的污名》這本書裡說,長期以來,非洲被強加的污名有,落後,野蠻。而這些施以污名的人以保護者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走了進來,取走這裡的金子和象角。
我們要隨時警惕那些先施以污名,再以保護者的身份出現的人,或團體。也要隨時警惕那些可能會被施以污名的污名。
Cover: 《這個世界土崩瓦解了》Things Fall Ap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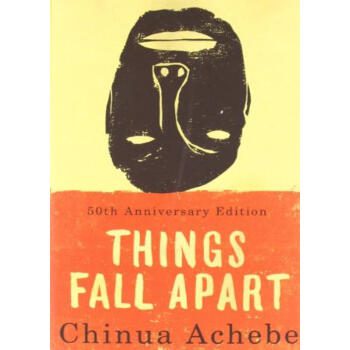
No comments yet. Be the first one to leave a th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