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布羅茨基在《怎樣閱讀一本書》中講,培養良好文學趣味的方式就是閱讀詩歌。
我讀詩並不是沖著培養良好的文學趣味去的。對我來說,詩是美,是音樂,是苦悶時的一縷清風。我喜歡詩的帶有音樂質地的語言、韻律和節奏。讀詩就好像在黑暗的屋子裡開了一扇窗,一下通體透亮起來。
我最近看了兩本詩集,一本是耶麥的《春花的葬禮》,一本是聶魯達Pablo Neruda的《疑問集》。
耶麥的詩我是第一次讀,讀他的詩,就好像欣賞一幅幅畫卷,是跟著詩人的一次愉快的旅行。
聶魯達不同,對我來說,年輕的聶魯達是愛情的,晚年的聶魯達是睿智的。後面這一特質則集中體現在這本《疑問集》裡。
從中學起就開始喜歡聶魯達,那時我情竇初開。
聶魯達一生為愛情和詩歌活著。他的很多情詩都是愛的絕唱,在全世界引起長久的回聲。
《你的微笑》:「你需要的話\可以拿走我的麵包\可以來拿走我的空氣\可是\別把你的微笑拿掉。」
還有《愛太短 遺忘那麼長》,等等,這些都在我青春歲月留下難忘的記憶。
他的《二十首愛情詩和一首絕望的詩》至今還放在我的床頭,我是讀了又讀。
現在,我的床頭又多了一本《疑問集》。我對他的理解也較全面了些,他不光是「情聖」,還是一個睿智的老小孩。
《疑問集》寫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共收錄了聶魯達三百一十六個追索造物之謎的疑問,分成七十四首詩,每一首由三至六則問題組成。
這些問題是聶魯達對人和自然,人和動物,乃至人和宇宙的關係的思考,這些「天問」帶著成人的經驗和孩童的純真。
這本詩集非常適合和孩子一起閱讀。這本書裡的每一個問題都可以拿來跟孩子一起作問答遊戲,對培養孩子愛思考、愛追問的習慣非常有益,同時,也可以充分開拓孩子的想像空間。
兒子嘉禾剛讀小學,對什麼都充滿了好奇。
我讀詩時,他常擠到我身邊問這問那。讀這本詩集,我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他童真、稚嫩的面孔。
現在只要有空,我就會把他叫到身邊,從中找出一首來跟他一問一答,他玩得樂此不疲。
我們指著園中樹上的蘋果問,這是什麼東西呀?孩子會答,蘋果。
其實我們提問,並不是我們不知道答案。有的是為啟發提問的人,有的只為尋求共鳴。
聶魯達這本詩集裡的這些疑問大部分在其心裡是有答案的。沒有答案的那部分都是他對人生的一種終極思考。
「世上可有任何事物,比雨中靜止的火車更憂傷?」
沒有看到這首詩時,我看到雨中的火車一定是漠然走過的,經他這麼一提醒,我心底的一種情緒就被調動了,我想起了很多比雨中的火車更憂傷的事物來,比如,站在高空細細的電線上的成排的麻雀,比如,細雨中獨自走在長長坡道上的孤獨的背影。
而我用這個問題問我八歲兒子時,他馬上說,「有啊,媽媽。雨中的稻草人就比雨中的火車更憂傷。」他說,稻草人很可憐的,特別是雨裡的稻草人。
為什麼呢?我問。
他瞪圓了眼睛,若有所思,「很大很大的田,只有稻草人一個在那兒,沒穿衣服,全身都濕透了,它一直一直伸著它的胳膊。很可憐的。夜裡也可憐。沒有人跟它作伴。」
和孩子一起讀會讓詩變得更充盈,讀詩人也會獲得更多的快樂。
「煙會和雲交談嗎?」
兒子說,「會的,就像我和小鳥交談,和蚊子,和蒼蠅說話一樣啊。」
聶魯達的這些「天問」之所以會受孩子歡迎,不光是他的語言直白,口吻也是孩子的。
「海的中央在哪裡?/為什麼浪花從不去那兒?」
「我能問誰我來人間,是為了達成何事?」
「燕子上學遲到了,會發生什麼事?」
這些問題,我兒子都曾經問過。
這本詩集體現了晚年聶魯達已參透人生,淡泊、回歸本真的心態。有些問題,集中了他一生的思考。
「為什麼海浪問我的問題/和我問它們的問題一模一樣?/它們為什麼如此虛耗熱情/撞擊岩塊?」
不用回答,我們知道生命就是這樣,在虛無裡生,往虛無裡去。「撞擊」是生命體征,「撞擊」本身就是幸福。
讓我們一起讀詩。至於怎麼讀,讀什麼詩,布羅茨基說,根據自己的趣味,去建造一個屬於自己的羅盤,然後去找你熟悉的特定的星星和星座。就像我喜歡里爾克、喜歡聶魯達,年輕的,老年的。
Cover: 《怎樣閱讀一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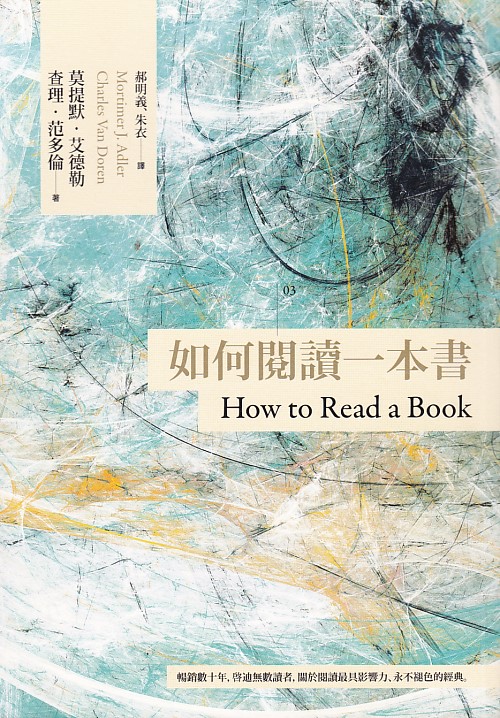
No comments yet. Be the first one to leave a th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