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緣于一位朋友的推薦。
那天我們在南山路上的西湖春天吃飯。我的朋友聊起了雷馬克。
他說,雷馬克雖然不是一線作家,但他的書真很不錯。
他特別提到了雷馬克的《流亡曲》。他說裡面有個細節對他觸動非常大。
他說,在那樣的年代,滿街都是吃不飽的人,他卻想給心愛的姑娘買花。想想,這種情況下,一個男人走在街上,手裡捧著鮮花是不是很奇怪,怎麼辦?他想來想去,用紙把一束玫瑰層層包起來,夾在腋下。
他說這個細節他記得特別清晰。
當天我在網上沒找到《流亡曲》,倒是看到了《西線無戰事》,便順手買下了,只是到現在才看。
這本書是寫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群德國青年在法國戰場上出生入死的故事的。故事從主人公「我」的視角展開。
看完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才知道什麼樣的細節才能觸動人心,什麼樣的文字,從不提悲傷,卻讓你悲傷到骨子裡。
克默里希一條腿中了槍,躺在野戰醫院裡,大家都知道,他是不可能再活著走出這間大病房了。
「我」和米勒一起去醫院看望克默里希。
米勒看中了克默里希那雙系帶的皮靴,並暗示克默里希,這靴子對他來說已經沒用了,而自己需要這雙靴子。
克默里希沒有同意。
米勒擔心克默里希突然死去後,靴子會落到衛生兵的手裡,他提出要守在病房外,等著克默里希死去。
看上去,米勒非常冷漠,心比鐵還要硬,在他心裡,似乎那雙靴子遠比克默里希的命重要。
其實不是,雷馬克說,米勒只是比別人更能看清現實而已。戰爭讓人變成了野蠻人。
雷馬克冷靜憂傷的敘述,讓讀它的人很難從中走出來。
「那時我們去司令部,一個班級有二十個青年,在去兵營前,大家還興高采烈地集體去理髮店刮鬍子,有的人還是平生第一次去。對於前途,我們沒有固定的計畫,極少數人對於事業和職業有想法,實際上不過是一種生存的方式罷了。我們仍然滿腦子都是模糊的觀念,在我們眼裡,這些觀念把生活和戰爭理想化了,而且幾乎賦予了它們一種浪漫主義的色彩。」
不知為什麼,讀到這一段,我的心就會隱隱作痛,那些逝去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歲月,就這樣一去不返了。
讀這一段,我就會想起北島老師《波蘭來客》裡的一段話:「那時我們有夢,關於文學,關於愛情,關於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可能就是裡面的那種調調吧,關於一去不返的過去,關於破碎的現在。
雷馬克的語言有一種特殊能力,有時你讀著讀著就笑了,但笑著笑著眼淚就出來了。
有一次,「我」和賴爾、恰登,還有克羅普四人在運河裡游泳,看到對岸有三個姑娘款款走過,我們突然春心萌動,決定深夜遊過運河,會會姑娘。
可姑娘只有三個,而他們四個。怎麼辦?他們決定把恰登灌醉。
可當他們三挾著麵包,遊到對岸,和姑娘溫存過後,準備返回住處時,卻看到恰登赤裸著身子,跟他們完全一樣穿著長統靴,胳膊下面夾著一包東西,飛也似的向前奔跑。雷馬克說,「他在全速前進。」
看到恰登「飛也似的向前奔跑」、「他在全速前進」這些細節時,就好像當時我也在現場,恰登的樣子太好笑了,可當我想到恰登為什麼那麼奔跑時,一切又都變得悲傷了。
在這本書中,還有一個情節非常重要,這應該是雷馬克最想表達的地方。
「我」去偵察敵情,被「囚」在了一個彈坑,不敢冒然離開,天黑了,有個人跌進彈坑,「我」用尖刀捅死了他。
在他掉下的皮夾裡,「我」看到幾封信和幾張照片。從照片上看,這是個普通人家的孩子,照片上的女人是他妻子,那小女孩是他女兒,那些信則是妻子寫給他的。
皮夾裡還有一本寫著他姓名的小本子,小本子上寫著他的職業——排字工人。
這之後,雷馬克用大段大段的文字寫「我」的內心獨白,寫到了「我」對戰爭的思考,我們究竟為誰而戰,為什麼而戰?敵人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敵人?敵人究竟是些什麼樣的人?
「大部分我都看不懂,實在太難了,而我只懂一點法語。但是我可以翻譯出來的每個詞,卻像一槍打進我的胸膛——又像一把刀刺進我的胸口……」
「我」決定以後要給他的妻子寫信,並發誓以後就以排字工人的身份活著,為她們而活,「我」要掙錢寄給她們,以求救贖。
遺憾的是,就連這個願望,他都沒有實現,他最終還是倒在了戰場上。而當天的報紙上寫著「西線無戰事」。
一定有一些人是活下來的,但活著的已經不再是過去的他們。
雷馬克在這本書的扉頁寫道:
這本書既不是一種譴責,也不是一份表白。它只是試圖敘述那樣一代人,他們儘管躲過了炮彈,但還是被戰爭毀掉了。
Cover: Pinter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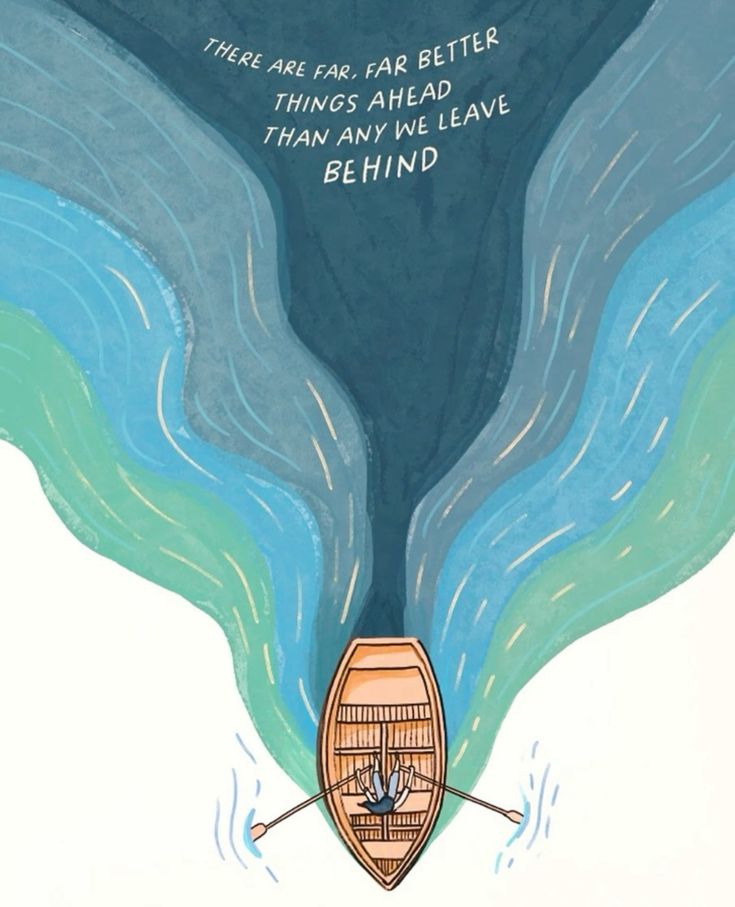
No comments yet. Be the first one to leave a thought.